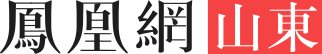随笔 | 尹桂瓒:姨姥爷王锡恩


独家抢先看
我母亲就一个亲姨,我也就一个姨姥爷。姨姥爷叫王锡恩,他去世整整五十年了,在世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很不起眼的农民,但这些年我却常常想起他,回想他一生的为人处世,觉得他的一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回味的地方。
记忆中的姨姥爷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瘦削的脸上总是留着不长的胡须,但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他的一生是为他的家人亲人活着的。
姨姥爷1900年出生在掖县西由镇新合村(那时叫西南庄子)的一个殷实的家庭,家里有地有房,虽不富裕但也是衣食无忧,弟兄四个老三夭折,姨姥爷排行老四,所以村里人都喊他老四、四哥、四叔、四爷爷。他父亲下世后母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十四岁时,遵母命跟着镇上的人到北京一家店铺做了学徒,出徒后成为了伙计,又遵母命回家成了亲。那时掖县到京城需几天的路途,车马劳顿的,掌柜每两年让回家探亲一次,上孝父母下续子嗣,但一直没有喜讯,直到过了三十岁后才收到家里的来信,说媳妇有了身孕,掌柜答应他等生孩子时破例让他回家探亲。急渐渐的熬到日子,家里打来电报说拾了个小子,就在姨姥爷兴冲冲地准备启程时,又收到电报,说媳妇产后大出血过世了。姨姥爷日夜兼程赶回家中,殡了媳妇,孩子这些日子跟二嫂带着,二哥二嫂有个大一岁的儿子叫璋,姨姥爷给儿子取名尧。大哥患精神疾病一直未娶,一大家子就靠二哥二嫂忙活,孩子不能老靠给二嫂,还得自己带在身边,还得有个娘照顾,所以姨姥爷重金托上媒人续弦,就这样姨姥娘急匆匆地嫁到了王家。
姨姥娘名叫卜兆花,是我母亲的姨妈,是朱桥镇招贤村人,也的确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秀花,高挑的个子,白净的脸盘,乌黑的辫子,模样俊俏受看,尤其是那一双精致小脚远近闻名,之所以甘做续弦下嫁,盖因年过二十,在那个年代已是正儿八经的老姑娘了,因挑得厉害媒人好久都不愿上门了。又因父母双亡,老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总不是事儿,也想该嫁出去了。姨姥娘从来是个有主见有远见的人,不计较自己的续弦身份,婚前就提出一点,嫁过来后带上孩子跟姨姥爷到北京过日子。那时的人都保守,都喜欢守家在地平静的过日子,姨姥娘愿嫁还愿跟着到北京,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姨姥爷自然愿意,也算是对丧妻之痛的慰藉。因前妻刚刚过世,婚事没怎么操办,就带上新媳妇和不满月的儿子匆匆返回北京。
掌柜无儿无女,看姨姥爷手勤眼快,为人厚道,待他如同自己的孩子,店里的大小事都交给姨姥爷打理。姨姥娘和老板娘也相处甚密,姨姥娘本来心灵手巧,给孩子雇了一位乡下逃荒来的小姑娘带着,姨姥娘就陪着老板娘打牌、品茶、下馆子、听戏、做针线活,这样的日子很适合姨姥娘的性格。可好日子不长,家里又传来噩耗,二哥去世了,姨姥爷的母亲捎信让他们回去趟。到家才知道,这两年家里遭遇了变故。先是大哥的疯病犯了,找了郎中开了药,越治越重,整天舞刀弄棍的伤害人,没办法只好把他锁在家里,六月十三西由的大庙会,他砸开房门跑了出去,拿了一把菜刀见人就砍,正赶上下大雨,那血水合着雨水在街上流,整个赶庙会的人都躲了起来,二哥想把他拉回来,拉扯中腹部挨了一脚,臂上吃了一刀,邻居都不敢出来帮忙,还是镇公所上的人骑马进城,到天黑时,县里来了警察把睡在庙门口的大哥带走了,关进了大狱。没过几天,可能是一脚把内脏踢碎了,二哥腹痛不治身亡,二嫂两年来惊吓不断,也变得呆呆地,娘家哥哥只得把她接回娘家,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老太太也卧床不起,一个好好的人家面临家破人亡。
姨姥爷一家三口回到家里,家里被大哥砸得乱七八糟,姨姥爷去城里看了看大哥,回来说人没几天活头了。又到二嫂娘家想接二嫂回来,二嫂说什么也不回来了,娘家正准备烧了七七给她改嫁,婆家都找好了。到地里看看,玉米地里的草比玉米还高。没过几天,大哥死在牢里,姨姥爷去城里拉回大哥的尸首落了葬。面对这种状况,姨姥爷的母亲听说二嫂要改嫁,说什么也不让把孩子带走,姨姥爷又到二嫂娘家接回侄子。然后和姨姥娘约好不回北京了,姨姥爷种地养家糊口,姨姥娘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面对诚愿跟着自己吃苦受累的媳妇,姨姥爷许诺姨姥娘,等孩子长大,他会把姨姥娘像娘娘一样供养起来。姨姥爷给北京的老板打了信,说明情况,感谢关照,并请老板帮忙处理退房卖杂物等一应事务,安心过起来了种田度日的生活。姨姥娘虽然娇贵惯了,但毕竟是个要强能干的人,很快就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责任,照顾老人,抚养着两个孩子。就这样寒来暑往十余载,老人古去,在姨姥娘的精心养育下,两个孩子长大,农闲时也送他俩到私塾去学点文化。等两孩子大起来,姨姥娘也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一生没能生下一儿半女。家乡解放后,姨姥爷两口先送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又送尧去北京做了学徒。
在以后的岁月里,姨姥爷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以他自己的方式养着宠着惯着姨姥娘,不让她沾手一点儿泥土活,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极少见的。姨姥娘在农村女人中也是比较另类的,她把京城里的习惯搬回了乡下,不同于那些村妇,她不串门,不聚堆,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喜欢把自己打扮的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喜欢喝茶打牌,喜欢做菜做衣服,屋里活都是好手艺,但她从不拿着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和一帮女人们凑一块,她做衣服的手艺只是用来做好料子,给出嫁的女儿们做婚服,给去世的老人们做寿衣。她做菜的手艺也只是在重大节日或别人家红白喜事去露一露。对于姨姥娘的这一切喜好,姨姥爷总是极力满足,他攒钱给姨姥娘买茶,姨姥娘懂茶,小时候就常听她念叨,福建的花茶苏杭的龙井碧螺春什么的,在文革前后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当地只能从大队小商店买到熏过茉莉花的碎茶叶末,姨姥爷就托人从外地捎来好茶,姨姥爷从没断了姨姥娘的茶。姨姥爷自己穿破旧的衣服,总是给姨姥娘扯布做新衣服,每年发的布票都是用在姨姥娘身上。每隔一段时间姨姥爷就赶集买来鱼肉,让姨姥娘做菜打牙祭。农闲季节雨雪天气,炕上一局扑克,灶间饭桌上一局棋,姨姥娘好玩,村里的老少爷们也乐意凑局,姨姥爷不参加,只是服务,到水炉上打来热水泡上茶,把炕烧得热热乎乎,赶上年节前后还会有炒好的瓜子花生招待客人。姨姥娘从来不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惹得村里一些妇女不满,文革中人称老明白的生产队长施运洪,曾对姨姥爷说,四哥啊,人家都攀比咱呢,让四嫂子到场院扒扒玉米皮儿干点轻活。姨姥爷没答应,为了堵她们的嘴,提出了农忙时他干两份活,晚上到场院看场,白天参加田间的劳动,替姨姥娘把那份活干了。看场晚上是要巡逻的,姨姥爷就一早一晚天明亮时迷糊会,中间坚持巡逻,困极了就在麦垛粮堆旁坐着打个盹,好在一年两季农忙看场院时间短,咬咬牙就坚持下来了,这样没坚持几年,姨姥爷岁数也大了,村妇也就不再追究了,姨姥爷也不再去看场了。姨姥爷坚持捡了一辈子的粪,每当清晨天朦朦亮,姨姥爷便束紧裤腰,撅着粪筐出门了,沿着公路有时走出好远,拾来的牲口粪人粪攒起来也顶了不少工分,这与他当年在京城店铺里穿着体面的长短衫站柜台热情招呼客人、打理店铺的情形判若两人,但是想到当初对媳妇承下的诺言,看到媳妇在他的呵护下,依旧绵柔娇嫩、面如桃花地生活着,他觉得一切都值了。所以在我们那条街上,那时的人都知道姨姥爷对姨姥娘好,这份好,让很多村妇眼热嫉恨,也为后来的父子关系埋下了祸根,成了二老晚年的一件堵心的事。
建国后两个孩子也先后成了家。侄子璋随部队南下,解放海南岛后就留在那边,后来转业到海南的广东省化工厂,还慢慢的成为了厂领导,找了个当地媳妇,生了孩子,由于路途远语言又不通,媳妇孩子从没回来过,只是侄子自己回来过几次,平日里有书信,有时也寄点钱回来。尧的媳妇是姨姥爷和姨姥娘在老家给他找的,也是个能耐人,结婚后就随尧到了北京,公私合营后跟着尧也进了工厂,慢慢也都进入了领导层,也是看不惯婆婆的生活习惯,但碍于面上还过的去,到北京后生了个儿子取名建国,是个聋哑孩子,小两口开始也带孩子回来看望过父母,父子关系的破裂源于卖房。
三年自然灾害,姨姥爷两口也遭受了饥饿的折磨,开始姨姥爷还坚持有口吃的先尽姨姥娘吃,但后来没有吃的了,也吃玉米棒和树皮磨粉蒸成的窝窝头,再后来连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两个人都病倒了,在生死线上挣扎,姨姥爷不忍心让姨姥娘眼睁睁饿死,一咬牙把房子卖了,那座房子在当年也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一个大院子,一座坐北向南的五间大瓦房,二哥婚后加盖了东厢房,大哥犯病为了关起来避免家人受到侵害又加盖了南屋,那个年代,就这么多好房屋也没卖几个钱,但是为了不让媳妇忍受饥饿,为了续命,更为了那句一掷千金的诺言,姨姥爷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后悔。房子卖掉了,老两口总算有吃有喝的活下来了,为此事两个孩子不算了,尤其是尧媳妇,一口咬定是后妈不为孩子留根,扬言不再回家不再认老人。到文革中那几年,尧的厂子来人政审,尧领着聋哑孙子回来住了几天,姨姥娘想方设法地给孙子做好吃的,姨姥爷也领着孙子下河摸鱼上树逮鸟,短暂的天伦之乐后,这爷俩回了北京又没了音信。
姨姥爷本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少年离家在外,很会看人看事,见谁都面带微笑,谁好谁赖、什么对什么错全都有数,平日不显山露水,遇到事情很有主张,邻居们都很尊重他,就连队长老明白也常常装上一袋旱烟,和姨姥爷聊聊队里的一些事。姨姥爷也很有骨气,从不低头哈腰,对于两个孩子的做法,不强辩不解释也不乞求谅解。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姨姥爷能干的活越来越少了,但还坚持拾粪,这是他唯一能胜任的农活。生产队一年两季分小麦和玉米,平日里分点鱼虾青菜,挣的工分不够是要交钱的,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无儿无女可以作为五保户,队里发给粮草,可姨姥爷有儿子,不能享受五保户待遇,生产队后来换的队长潘福元叫姨姥爷四爷爷,几次要派人以生产队的名义去北京找尧说理,也鼓动姨姥爷去到尧的单位告他们不养活老人,姨姥爷都不让,他一直说那样他们就没法做人了,他坚持拾粪、硬撑着跟着青壮年参加劳动,队长没法了,麦收结束后,安排队里的人将姨姥爷送到潍坊又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让姨姥爷自己去找儿子好好说说,姨姥爷也想去看看儿子,打了个电报告知到达日期就坐车去了北京。大概十天左右,姨姥爷背着小布包回来了,从他断断续续的表述中得知,到京后被一个叫他爷爷的年轻人(可能是二孙子也可能是孙女女婿)接到一个招待所,给了他一把饭票,让他先住下,说家里有点事,过两天来接他。在招待所住了两天,姨姥爷试图去找他的儿子,但他离开北京四十多年了,北京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转到深夜既没找到单位也没找到儿子家,遇到个好心人按照他所住招待所钥匙牌上的名称把他送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姨姥爷打听着到了火车站,买上到潍坊的火车票,到潍坊后又坐汽车到平里店,然后走了近二十里回到了家。
这次北京找儿子,儿子没见到,姨姥爷却变了个人,一下子苍老了,干瘦干瘦的脸上木木呆呆,两只眼睛也灰暗无光,常常坐在那里自言自语,说得最多的就是房子,说房子在人没了,要房子有什么用啊!去北京时是盛夏,转眼秋风凉了,就这样时好时赖的两个多月,姨姥爷得了中风昏迷在炕上,公社医院的大夫也来看过了,说没有救了。在炕上又喘了几天,什么也不会说,最后的时刻醒了过来,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姨姥娘,当时我母亲在场,是他们身边唯一的亲人,母亲说我知道你丢不下俺姨,你放心,俺姨有我们一家,我给她养老送终。听罢母亲的话,姨姥爷闭上双眼,急促的喘了一阵后,撂下了那句比金子还重的承诺,停止了呼吸。
生产队长领人来帮忙办理姨姥爷的后事,正赶上土葬改火葬,又经历过文革破四旧的洗礼,没有仪式,没有披麻戴孝,也没有车马纸幡,但停灵守灵、上庙送魂、孝子摔盆还是保留了下来,在我们那一带外姓晚辈是不给长辈带孝的,因为外姓人不属于家族孝子孝孙序列,但母亲说不管这些,领着我承担起孝子的一切活动,给他的儿子侄子都拍了电报都没有回信,天气还是夏末初秋,遗体不能久停,母亲和队长意见一致,不等了,联系了县火葬场约定第二天上午来拉人。姨姥爷在家的最后一夜,正是中秋节,母亲婉言送走了队里在这守夜的人们回家过节,安置姨姥娘睡下,领着我守灵。
中秋夜夜深人静月光清冷,院子里的老槐树树影斑驳,微风吹过枝叶摇曳,在院子里划过一道一道的光影,恍惚间感觉是姨姥爷的灵魂在游荡,我有些害怕,和母亲一左一右坐在姨姥爷的灵前,没有棺木没有灵牌,一张黄纸盖着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姨姥爷,母亲重新换上香,在灵前的泥盆里烧上纸,轻声细语的给我讲着姨姥爷对我们的好。迷迷糊糊中,我眼前也浮现出封门大雪中姨姥爷替我们扫雪开门;母亲外出开会姨姥爷陪着我度过漫漫长夜;生产队分麦草,我推着满载车麦草的小推车,因不会装车半路撒了一地,姨姥爷闻讯赶来帮我重新装好送回家;一次我吃水库的鱼吃多了上吐下泻,姨姥爷半夜背我去医院,战战兢兢踏过河水漫过的龙泉河桥……。朦朦胧胧天渐渐亮了,母亲叫醒我,又重新换上香,烧上纸,然后开始做饭、准备火葬和埋葬的东西。送姨姥爷走是母亲摔的灰盆,看到妈妈那瘦小的身躯猛然举起纸灰盆狠狠摔下的一瞬间,我突然泪崩,泪光中,一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好青年,一个责任在肩、勇挑重担的好儿子,一个爱妻如命、一诺千金的好丈夫,一个爱子心切、不计前嫌的好父亲,妈妈的好姨父,我亲爱的姨姥爷,静静躺在灵车中缓缓驶出家门,驶向一个让他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他太累了。
那是1974年秋季,姨姥爷74岁。
后续
一个周后,姨姥娘收到的侄子璋的10元的汇款单,没有信。两年后,姨姥娘改嫁给了邻村龙泉大队的潘春圃,这又一次证明了姨姥娘的眼光和智慧。潘春圃是烈士,唯一的儿子牺牲在战场上,潘又是早年参加过西海军区打过仗的老人,公社大队都照顾的很好,几年后潘过世,因姨姥娘没抚养过牺牲者,不再享受烈属待遇,又无子女,按照政策改作五保户,村里给粮给草,终生的生活有了来源。我们的照顾不再是雪中炭而是锦上花,这样她的晚年既有基本保障又有亲人陪伴,就等于她自己给自己的晚年加了双层保险。
到了九十年代初,璋回来了,他已经退休,打听着找到姨姥娘的新家,这时潘春圃已经去世,璋陪着姨姥住了一个多月,对于侄子的到来姨姥娘波澜无惊,母亲曾经说过,姨姥娘心硬眼硬,从没看到过给谁服软,也没看到过流泪,即便你姨姥爷走也没流一滴泪。娘俩平静相处,谁也不提往事,谁也不揭伤疤,一切都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璋提起小时候姨姥什么做的好吃,姨姥娘就做给他吃,瓤儿饼糖火烧,羊肉饺子烩里脊,来的时候正是春天开海,每样海鲜娘俩都买来吃,只要侄子说,姨姥娘就做,虽年已八十,但做出来依然色味俱佳。侄子也不断到集市上买新鲜的鱼肉蔬菜各种瓜果给婶母吃。天气晴和也领姨姥娘出去转转,田野间水库旁,据邻居说看到他自己也去过姨姥爷的坟地。母子俩融洽和睦的相处了一个多月,临走的那天晚上,姨姥娘炒了几个菜,侄子买了瓶好酒,母子对酌,酒过几巡,侄子先开口了,他恭恭敬敬的给姨姥娘磕了头,然后承认不该为卖房子的事与老人翻脸,他也告诉姨姥,姨姥爷去北京时尧已瘫在床上,是挨批斗被红卫兵打在腰上造成的截瘫,老人来北京的事媳妇没告诉他,媳妇对他不好,他喝药寻短见被救了回来,为此事哑巴儿子与他妈反目离家出走,几年后才从郊县的一个林场找回来,后来尧还是自杀了,是在暖气管子上吊死的,自杀前写信给他哥,托他回家看看,这信璋带的,他读给姨姥娘听,在信中他拜托璋以后一定要回家看看,如果老人还健在替我赔个不是尽尽孝;如果老人不在了,请到坟头替我上柱香,烧刀纸!璋说这一切时姨姥娘没激动,她只是平静的听着,听完也平静的告诉侄子,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了,不提了,房子毕竟是为我卖的,被我吃了喝了,我俩活下来了,能活着看到孩子们都好就值了。璋回去的时候我母亲已经随我们在烟台居住,璋也请姨姥娘转达对姐姐(母亲比他俩都大,小时候也一块住过)照顾老人的感谢。这一切都是后来姨姥娘告诉母亲的,姨姥娘说,她见到侄子真的没气,他能回来看看我也算是有良心。璋回海南几个月后,侄子的孩子给姨姥娘寄来一信,原来侄子来时已确诊为癌症晚期,侄子放弃了治疗回来陪陪老人,从烟台又去北京看了看尧媳妇和孩子们,回海南后不久就走了。
姨姥爷去世后的年月里,我们一家履行了承诺,认真的照顾着姨姥娘,母亲每年都回去陪姨姥娘住段时间,我们兄弟姊妹也常常回去看望老人,也委托我们各自的朋友照顾姨姥娘,姨姥娘无忧无虑高高兴兴的活到94岁,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