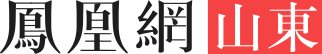【烟台年 烟台味】⑱拜年往事


独家抢先看

每逢春节,我都会想起小时候拜年的往事,那些生动热闹的场景,像一堆花花绿绿的糖果,珍藏在记忆深处,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都散发着甜美的味道,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莱阳市最北端的一个山村,地处偏远,物质匮乏,平时连糖果都很少吃到。一入冬季,雪花飘起,小孩子就开始盼望过年。过年真好啊!放鞭炮,穿新衣,吃好饭,特别是五更拜年,简直就是孩子们的狂欢。

大年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一家人一起守岁,彻夜不眠。午夜十二点,男主人到院子里放鞭炮,迎新年。放完鞭炮,家里的晚辈要先向长辈拜年,长辈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女主人在厨房做菜、下饺子,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五更要吃饺子和鱼。五更的饺子里包着硬币、糖果、大枣、栗子,吃到这样的饺子,寓意着来年能挣到钱、生活甜美,孩子们往往为了能吃到钱多吃好几个饺子。五更吃鱼寓意“年年有余”,因为鱼有腥味,也被人们说成谐音“兴兴”,寓意新的一年兴旺。
吃了五更的饭菜,大人和孩子都穿上崭新的衣服鞋袜,女主人和老人们在家里迎接来拜年的人。年纪小的孩子跟着爸爸外出拜年,年纪大点的孩子与本家族的兄弟姐妹们集合,成群结队外出拜年。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孩子,我们家族的兄弟姐妹汇集到一起有近二十人,农家的小屋空间狭窄,容纳不了拜年的大队人马,于是,前面的人进屋问好,后面的人就站在院子大声问好。

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期,我们村还没有通电,街上黑乎乎一片,屋子里灯光温暖,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硝烟的味道。人们穿梭于街头巷尾,去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拜年。问好的声音、应答的声音此起彼伏,农家屋里的煤油灯或蜡烛映照着一张张笑脸,热情的问好声或应答声传遍寒冷的夜空。
若是下过雪,脚踩在雪地上会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冷风吹在手上和脸上,心里却洋溢着温暖和快乐。难免有人因脚下的雪不小心滑倒,即使是年岁小的孩子不小心摔倒也不会哭,旁边的人会把摔倒的人扶起来,打趣道:“过年了,你拾了个大元宝。”周围的人也都善意地哈哈大笑,拍拍身上的泥土或雪花,大家又兴高采烈地走在去拜年的路上。

小孩子最喜欢拜年,喜欢成群结队的热闹,喜欢黑夜行走的神秘,更喜欢到了哪家拜年都会得到糖——虽然嘴上推辞“不要,不要。”去拜年的那家大人通常都会抓着一把糖追着塞到孩子们手里,有时甚至会追到院子或门口。我那时年纪小,分到的糖格外多。每当兜里装满糖,我就高兴地回家把糖仔细放好,再出去拜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糖。孩子们也都会互相比较谁得到的糖更多、哪种糖更好吃。有位本家的伯伯每年过年前都到山上打野兔,过年包兔肉饺子,这在当时是很少吃到的美食。去他家拜年,热情的伯伯总是让我们尝尝他家的兔肉饺子。
老家的人们讲究辈分,按照传统习俗,拜年只能是晚辈给长辈拜年,这是农村特有的文化。我们家族的辈分在村里最大,村里的大多数人叫我的父母那一代人为“老爷爷”“老奶奶”,我和同辈的兄弟姐妹从一出生就被人叫“小爷爷”“姑奶奶”,我们从小就叫很多中老年人为“孙子”“侄子”,叫他们的老婆为“孙媳妇”“侄媳妇”。
小时候,我和同辈的小伙伴都不喜欢自己的辈分大,觉得出门论辈很麻烦,特别是一到拜年,我们这些辈分大、岁数小的孩子就会有些无奈地想:辈分这么大干什么?过年都不能挨家挨户要糖吃。
我有个邻居那时四十多岁,论辈分,我叫她“侄媳妇”,她知道我喜欢糖,就逗我:“你问我过年好,我就给你糖。”因为她和我的妈妈年纪相仿,我岁数小,没有觉得给她拜年有什么不妥,于是毫不犹豫地说:“侄媳妇好。”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当时在农村,辈分大的人给辈分小的人拜年问好,会被人当做笑话。
来源:烟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