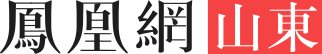【烟台年 烟台味】⑯“出门”


独家抢先看
“出门”,是正月里走亲戚的特指,那时侯,走亲戚叫“出门”。
既然是走亲戚,那就不能空手而去。记忆里,走亲戚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大枣饽饽了。

那个年代,母亲总是省下那点白面,留着过年多做几个饽饽。用纯白面做一锅大饽饽,留着请客和“出门”用,我们自己吃的是用一层白面包着黑面做的,蒸熟后掰开,白皮黑瓤,是真正的“白加黑”。不爱吃也没有办法,大白面饽饽除了过年前几天能捞着吃点,绝不会管饱外,其余的饽饽就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那是留着请客和“出门”用的。
大饽饽十分珍贵,每次“出门”,母亲都非常细心地清点篓子里的大饽饽,数数要去的亲戚有几家,装饽饽是有讲究,比如,去三个舅舅家,就要算算装几个饽饽合适,因为正月里是很忌讳单数的,要保证上一家留过饽饽以后,到另一家还是双数,甚至,在三个舅舅留过饽饽后,我们回家时,保证篓子里也是双数才行。这真的有点费脑子,留饽饽的亲戚,也要看清饽饽的个量,掂量着留,一个或者两个。

有一年,我跟着哥哥去姥姥家,先拜见姥姥以后,就要背着篓子去三个舅舅家,依次是大舅、二舅、三舅。那年,大舅家去了很多亲戚,满满一屋子,我和哥哥问过好之后,就坐立不安了,想赶快去二舅家,大舅母便急匆匆在篓子里拿了一个饽饽,我们就去二舅家了。
看见我们来了,二舅母十分热情地接过我哥哥手里的篓子,招呼我们吃糖,吃炸果子,眼看快11点了,我哥便催促二舅母留饽饽,因为正月“出门”是不能过午去的,待二舅母掀开篓子上面的花毛巾,篓子里是五个饽饽,她的脸色当即就变了。她叫过哥哥,指着篓子里的饽饽对他说,你数数,这是几个饽饽,哥哥看了,也脸色通红,仿佛干了天大的错事一样,小声地说,我们去大舅家,大舅母只拿了一个饽饽,并解释说,大舅家亲戚多,大舅母也没点数,不是故意的。那时候,哥哥个子已经很高了,也懂事了,不像我,还傻傻地站在那里笑颜如花。

大正月里,还能咋地?二舅母把自己家的饽饽给我们拿了一个,放进篓子里,凑成了六个饽饽,叫我俩赶快去三舅家,别晚了。
三舅没舍得留我们的饽饽,又给篓子里放了一瓶酒,对我们说,这酒是地瓜干酒,好喝,捎一瓶给你爹。
我俩在三舅家吃饱喝足,又回到大舅家,大舅母听说留错了饽饽,狠狠拍了自己的大腿两下,自责不已。她赶紧下炕,装了两个饽饽一包桃酥去了二舅家,跟二舅母解释道歉。

小时候,家里的食材都很珍贵,到了正月,要宴请左邻右舍和平常对自已有恩情的人,亲戚也多,你来我往。母亲嫌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闹哄哄,还总馋嘴,大多初一就打发哥哥领着我们弟妹三人走亲戚,依次是姥姥家、姑姑家、姨姨家,还有一些偏亲等等。我们家的食材留着招待客人,那我们兄妹四人也去别人家蹭点油水吧。其实,无论走到哪家,招待客人的菜大多数是固定的老四样:一盘猪头肉拌大白菜,一盘猪皮冻,一盘白肉片粉条,还有一盘豆腐。再加菜,就各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了,有的是刀鱼或鲅鱼,或者是肉炒胡萝卜什么的,偶尔能吃到炒芹菜,也是秋天培在沙子里保存的,口感已经很老了。不像现在,大棚蔬菜应有尽有。
文/衣延平
图/小草、柳延忠、王淑云 、纪学山
来源:烟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