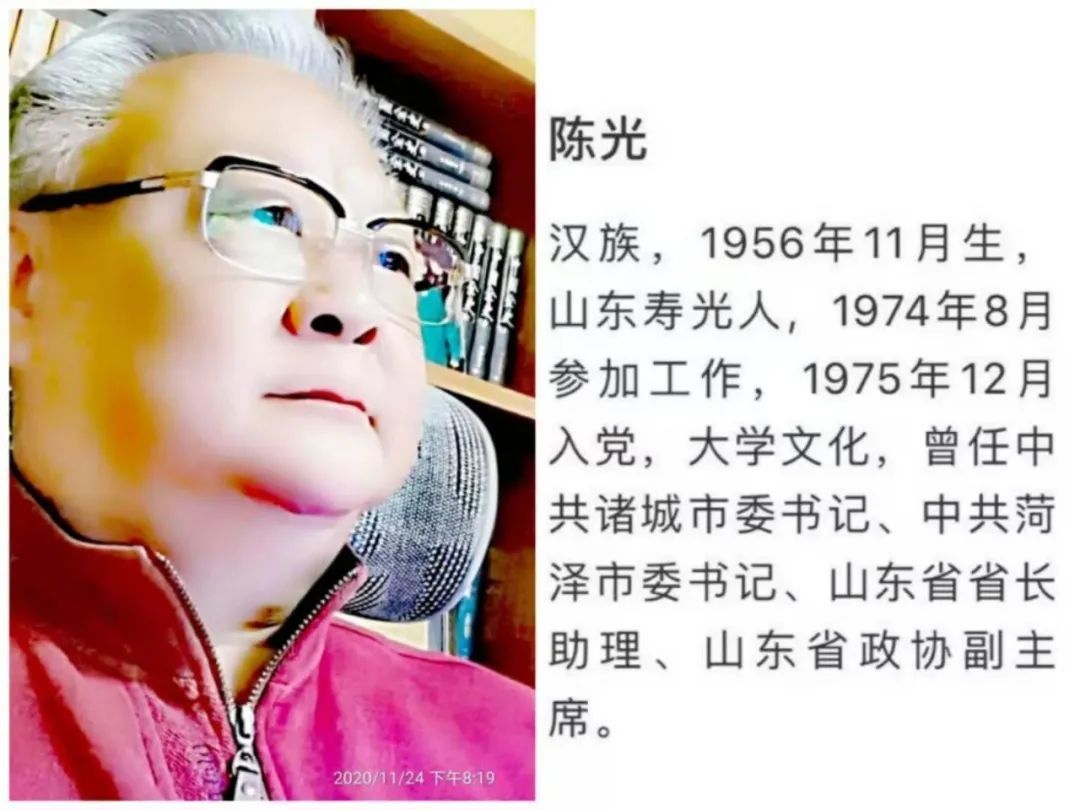陈光:书之情


独家抢先看
朋友问:“除了工作,今生你最钟情的是什么?”细细想来,应该是书。
我爱读书,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更没有报纸,唯一能让人长见识得乐趣的就只有书了。从识字开始,就嗜书如命,不管什么书,拿到手就如获至宝,不连夜拿下总不算完。常常父母那边都起床了,自己小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
后来生活环境变了,现代传媒多了,自己人也年过不惑,但对书的感情依然不减。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娱乐的,依然是见缝插针,有空就读,唯一的变化,是小说读得比过去明显少了。有时听人说起某部作品好,便急匆匆上网去查,然后赶快托人去买。1998年央视一套热播电视连续剧《雍正大帝》,看了前三集就摘不下眼镜,急不可耐买来了二月河的原著,一套三本,坐下就读,恰逢周末,竟然36个小时除了吃喝没合眼没挪窝,一气读完。那感觉,用句时髦的话:真爽!当然也有“不爽”处---合上书本,两眼昏花,竟然好长时间看不见东西。现在想起这事来,自己都觉得好笑。
小时候读的书,绝大部分是借别人的。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听说谁有一本好书,不亚于如今的彩民中了头彩,爱车族弄到部好车,总要千方百计搞到手。有時为借一本书,要跑十里八里;有时还得低三下四看人脸色。借到手后还要分秒必争,过了约定的时间要受处罚的。还要注意爱护,不能弄脏,不能撕破,更不能丢失,不然处罚会更重。人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话我是深有体会。进得大学门,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办借书证,看到学校图书馆那么多书,兴奋的一连几天都觉得太阳比过去亮,天空比往常蓝。
不光借过书,我还“偷”过书。文革初期,我10岁,上小学4年级。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就住在公社的中心小学里。那时候校长整天挨批斗,学校乱成一锅粥。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在一间上了锁的偏僻小房子里面堆满了书。这一发现,对于我绝对是“老鼠见了大米”,不觉两眼放光,口水直流。赶快找来竹竿和铁钩,用麻绳儿绑好,瞧瞧四下无人,便把竹竿伸进窗户……那窗是旧式木结构,柃子很密,窗口很小,要勾出一本书来绝对不容易,往往累得两臂发麻才勾住一本。更令人丧气的是,眼看到手,又中途滑落。谢天谢地,终于拖出一本!揣到怀里,迫不及待跑回家去读。就这样,几天读一本,读完了赶紧扔回去,再勾出一本来读。对毛主席发誓,我只是偷出来读读而已,一本也没有据为己有。我清楚地记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几本经典著作,都是那段时间偷出来,半生不熟、囫囵吞枣读的。50多年过去,这个秘密从没对人说过,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好笑。
我听过说书人说书。那时候的农村,生活单调乏味,唯一的文化传播就是说书。冬天的夜晚,和小伙伴们跑到生产队的牛棚里,小板凳一坐,和大人们一起听瞎子说书,那真是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夏天当然是在村中的场院里了。说书的瞎子也很会来事儿,说到最紧要处立马打住,让你满脑子想着,一颗心吊着,第二天晚上还得搬个小板凳,早早来此等着。前几年看电视连续剧《大染房》,剧中有个人物叫陈六子,大字不识一筐,却世事洞明,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他自己说,所有的本事都源于小时候听说书,对他的说法我是很认同的
我自己也说过书。从小记性好,虽然算不上过目不忘,但凡读过的书,听人家说过的书,情节总能记个八八九九,有时不免想卖弄卖弄,为此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那是读高中的时候,在校寄宿,全班40多人一个大宿舍。晚上自习后学校吹哨熄灯,年轻人睡意不浓,你逗我闹,胡吹海嗙,我便摸黑给大家说书---或《封神演义》,或《岳飞传》,或《三侠五义》、《今古奇观》……每天几回,人模人样,也是“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也是“要知如何如何,切听下回分解”,赢得不少同学喝彩。
乐极生悲。后来不知什么人告状,校领导窗外偷听,一下被逮个正着。这还了的!传播封资修,歌颂旧王朝,向往旧社会不是?想复辟不是?不光写检查,还要大会作检讨。进步同学奋起批判,自己唯有低头诺诺。幸在学生一个,又无其他“劣迹”,也没受什么处分。40多年过去,当年的老师都已年过古稀,同学也都已花甲了。偶尔见面说起此事,很多人还说我读书多,记性好,有口才,好多故事都是从我那儿听来的,我是哭笑不得!
我喜欢买书藏书。上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了,自己有收入了,能挺直腰杆进书店了,不用再理会书店服务员的白眼了,最大的喜好便是逛书店。那时的工资收入,除了吃饭穿衣,不吸烟不喝酒,剩余的钱,几乎都买了书。到结婚时已经装满了几个纸箱子。父母问希望要什么家具,我说其他可有可无,但一定要帮我做个书橱。
一直到现在,无论在机关上班,还是到外地出差,稍有闲暇,便去书店走走。但凡碰上好书,不管贵贱一定是要买的,2004年4月到台湾考察,在台中市的一个商场,见到了台湾出版的山东作家张炜的新作《你在高原•西部》,繁体字,竖排本,不看价格立即掏钱买了一本。回来后打电话告诉作家本人,张炜也特高兴,有亲笔签名送我一本大陆出版的。
这里想发点牢骚的是,现在的书实在品种太多,让人眼花缭乱不说,而且良莠不齐,价格昂贵,让人既伤脑筋又倒胃口。曾经上当买过几回盗版书,颠三倒四,错字连篇,不忍卒读,气得我把它撕个粉碎,扔进了垃圾堆。
我喜欢送书给别人。这些年来,我这个自视清高轻易不给人送礼的人,却经常买书送人,当然是那些爱读书的要好的朋友。不喜读书的人是绝不送的。我参加工作早,有固定收入時,很多爱读书的高中同学,还在贫困中挣扎,我就买书资助他们,以书为桥与许多同学结下了手足之情,至今念念不忘,联系不断。2007年元旦前夕,一位在厦门工作的同学来访,畅叙昔日情谊,还拿出我在1979年他读大学时我寄给他的英汉小词典,说他一直在身边珍藏着,我听了自己都觉得感动。前几年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变革中国》,读来觉得很不错,便一次买了20本送给同事。好的精神食粮与大家共享,确是一件乐事。
不得不说,这些年地位变了,条件好了,收入高了,反而接受别人送的书多了,自己送给别人少了。事务繁忙,岁月倥偬,有时本来想好给哪位朋友送几本书的,却一拖几个月也没有送出,每每念及此事,深有愧疚之感。
我写过书。长期从事调查研究和文字工作,对当代的改革和发展有一些粗浅的认识,也积累了一些资料。经朋友怂恿,前些年试着写了几本小书,竟也出版了。我不知道书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我只知道,许多人给的好评,有很大成分是出于面子的恭维。当然,我敢保证,文章绝对是自己写的,是经过自己深入思考的,印刷出版的费用也绝对是自己掏的。没拉过一分钱赞助,也没动用关系卖过一本书,都是无偿赠送于人的。心底无私,虽坦坦荡荡,细细想来却也有愧:就自己这点墨水,你说著的个什么书呢?
我也编过书。开放的年代,人人都敢编书,就连我这个哪个学科都不精的人,前些年赶时髦居然也编过几本书。凭心而论,不是胡编乱造,不是人云亦云,不会误人子弟,不会把人引入歧途,但水平绝对不高,也绝对没有赚人家的钱。鲁迅的名言: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我時有疑惑:编那些用处不甚大的书,算不算浪费别人的时间呢?自己今后打死也不干这样的傻事了。
我还评过书。绝大部分是为别人的书写的评论文章,或写的序言。而且绝大部分是受朋友或同事的邀约,不写推脱不过。文章谈不上深刻,更说不上华美,可朋友总说,你的文章为拙作增光,添彩不少。我笑笑,心里说,自己扒几碗干饭自己知道,别说添彩,但愿没给你拉色就好。
古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是俗了,但“开卷有益”这句话,却是对的。
马克思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巧慧,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读哲学使人思索。精神上的缺陷,没有哪一种是不能由读书来补救的。
以我自己的经验,让你乐让你爱让你聪明让你顽强让你百折不挠让你积极向上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书。书不仅可以给你知识和力量,还能给你品格和人生的方向。
我爱书,真爱!
如有来生,我愿做一个图书管理员,像一只鸟,在书的天空里翱翔;像一条鱼,在书的大海中畅游。
(2006年10月于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