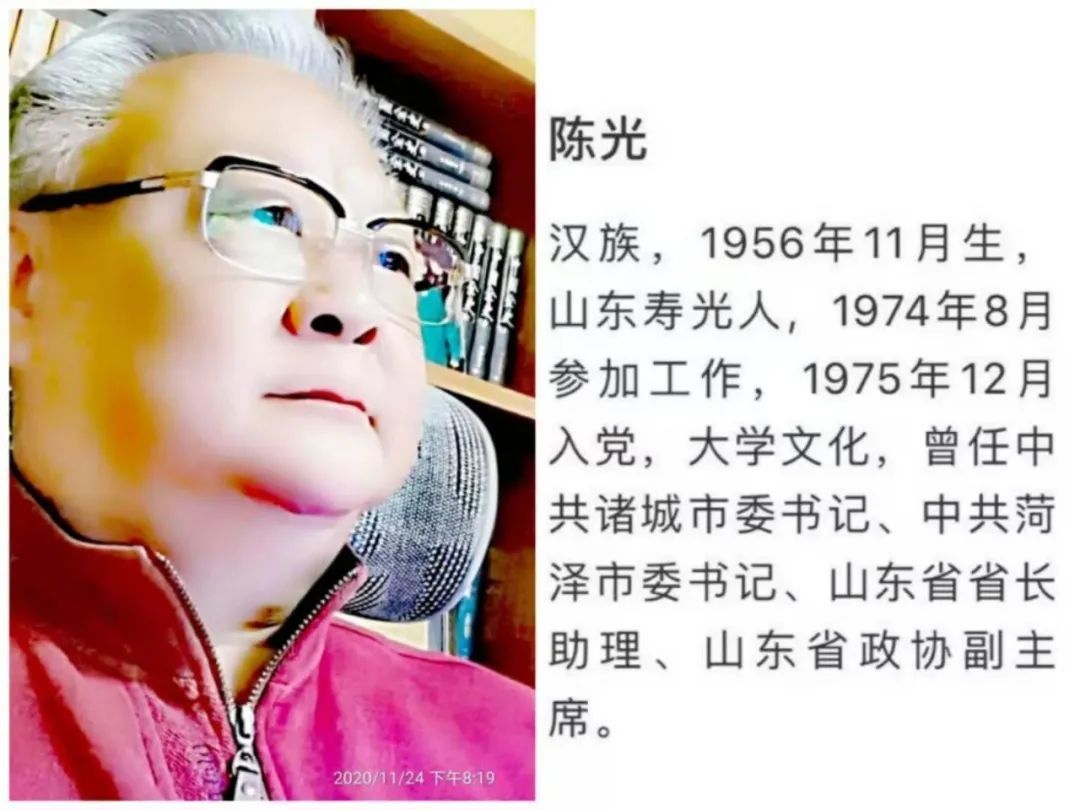陈光:盐工情


独家抢先看
盐,人类每天必须食用的东西,官称食盐,俗称咸盐,民族地区叫盐巴。所谓盐工,当然就是生产食盐的工人。许多地方把盐场里的人统称为盐民。在我的老家寿光县羊口镇,镇上的人一直看不起盐场的人,他们把制盐叫“晒滩”,把盐工叫“滩汉”,把我们这些盐工的孩子叫“滩汉料子”。我的父亲是老盐工,我自然就是“小滩汉料子”了。在羊口镇上学的时候,我和同学走在路上,時常会看到人们投来鄙视的目光,经常会听到有人指着我们叫“滩汉料子”。我们不做声,也不生气,我们并没有觉得做盐工不好,也没有觉得镇上的人比我们高多少。
现代科学证明,盐,与水、空气、阳光和食物构成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五大要素,盐与生命密不可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不断地摄入一定数量的盐,使体内经常保持足够的盐分,才能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心脏才能正常工作,血液才能正常流动,筋骨和肌肉才会有劲。如果人体内的盐分失掉一半以上,未能及时获得补充,就会出现肌肉疼痛、抽筋恶心、休克昏厥等许多症状。
如果说水是生命之源,那么盐就是文明之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盐,凭借其独特的美味,吸引着人类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城邑。多少部族、城邦和国家,因盐而战,因盐而兴,也因盐而亡。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朝代,食盐成为盐民的生计、商人的钱袋、官府的金库。食盐的营销的管理,自然是历朝政府的重要政务之所在。盐粒虽小,盐法很大。细碎的盐粒,严峻的法律,曾经有人因为从盐场私带了一粒盐而被盐官杖杀,古代盐法之严峻,远不是现代人所能想象。
山东省的寿光县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制盐历史悠久。寿光北部的渤海边上有四个大盐场,面积上千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海盐和井盐生产基地。从12岁起,我就生活生长在这里。从14岁开始,我学做盐工。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生活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是刻在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
往事并不如烟。父亲从上世纪60年代就在盐场工作,是老盐工了。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长期生活在农村,我是在60年代末跟随父亲到了盐场。父亲工作的单位是卫东盐场老八队。卫东盐场五十年代建场時叫寿光县合作盐场,是县属大集体企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叫卫东盐场。盐场在羊口镇周边,北面是小清河,东面是大海,自东向西共十个大队,绵延30 公里。之所以叫老八队,是因为地处老场区,后来场里又建了新场区,不再称队,叫工区。
老八队规模很小,孤零零的两排砖瓦房躺在盐碱滩上,周边十几里荒芜人烟,除了职工宿舍和一间食堂,其它什么都没有,买一根针一条线也要跑十几里路。盐工几乎全部是单身,家属都在农村,是农民。队里只有一户“双职工”,就是夫妻都是盐工。男的姓周,他家女人做炊事员,儿子叫周义,与我一般大。父亲和十几个工友住一间大宿舍,每人一张单人床。在父亲的床边塞了一张小床,就是我的住处了。没有桌椅,也没有橱子,我和父亲有点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堆在床底下。白天,父亲和工友们下滩干活,我和周义结伴去场里的职工子弟学校上学。学校在场部,步行要一个多小时。我们每天早起吃饭,6点出发。书包里放一个窝头、一块咸菜,中午在教室里凉着啃,这就是午饭。下午放学回来,趴在床上完成作业,然后与大人们一起吃晚饭。叔叔们用废旧材料制作的小饭桌摆在宿舍中间,每人一个小板凳或者小马扎,有的干脆在地上蹲着。饭菜极其简单,食堂做什么吃什么,一样的馒头或窝头,一样的咸菜,一样的粥,没有任何选择。偶尔有人回家探亲捎回来一点家乡特产,或者有人去场部办事买回来一包点心、一瓶酒,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全屋最高兴的时候了。宿舍里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书籍,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晚饭之后,各人在自己的床上抽烟、想心事,很少有人说话,然后就是静静地休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盐场的夜很长。清晨四五点钟醒来,躺在被窝儿里不动,望着渐渐发白的窗户发呆。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也这样生活,更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不是很精彩。老八队,让我学会了保持沉默、不怕孤独、忍受寂寞。
盐场的星期天不休息。盐工每人每月四天假,攒起来一起休,为的是便于盐工回乡探亲。也可以把自己的假期借给或者送给别人。谁家里有了大事,可以借用别人的假期。盐工们都很团结,也很义气,这种事经常发生。每到周末,我便顶替父亲下滩干活,换下父亲洗洗衣裳,稍做休息。周义则是替他母亲。这是盐场不成文的规矩,允许孩子星期天替大人干活,相当于一种福利。我那时年纪还小,个子很矮,力气不足,充其量算个半劳力,叔叔们便让我干轻活。我很过意不去,觉得这是赚了别人的便宜,便早出晚归,尽力去干,而且认真学习手艺,很快掌握了许多盐业生产必需的技术。
让海水或井水变成盐,是最神奇的过程。最早的制盐方法是煮盐,早在神农氏时代,寿光北部的夙沙氏部落首领,用陶钵装满海水,放到火上煮。海水煮干后,钵壁上出現的白色粉末,就是最早的食盐,煮食物時加入,感觉微咸,使人兴奋,让人浑身充满力量。夙沙氏“煮海为盐” ,开创了华夏制盐历史之先河,被称为盐业之鼻祖,史称盐宗,备受推崇。到清朝乾隆年间,制盐方式演变成了“晒盐”,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谓“晒盐”,就是选择大片平坦的沿海滩涂建设盐场,也称盐田。即在海边用挖土筑堰的方式,建设一大片盐池子,盐池分成两部分:蒸发池和结晶池。蒸发池很大很深,每个面积几千平方,蓄水上千立米。结晶池稍小,也比较浅。池堰和池底用厚厚的红泥抹平,确保海水不漏。生产过程是,先将海水引入蒸发池,通过日晒蒸发水分,让海水的含盐量不断增加,变成“卤水”。衡量卤水浓度的标准是“波美度”,测量浓度的工具是“重表”。卤水浓度达到25度,就成为饱和卤,继续蒸发,盐就会从水中析出。生产过程中,将即将饱和的卤水放入结晶池,继续日晒,不用几天,食盐就会在水底迅速结晶,迎着阳光,闪闪发亮,那就是盐粒。先是薄薄的一层,眼看着一天天变厚,会达到十几厘米。这时候,用特制工具将其捞出,得到的就是原盐了。国有企业羊口盐场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年产量达到数百万吨。卫东盐场、岔河盐场、菜央子盐场用的则是井水制盐。就是先在盐碱滩上打井,然后用风车和水车把水提到地面,后面的工艺则完全相同。相比而言,地下卤水浓度更高,生产的原盐也更洁净。
盐场每年的生产分为“春晒”和“秋晒”两季。每年三到五月前后是“春晒”,是盐业生产的黄金季节。这三四个月,风和日丽,阳光充足,气温升高,而且少雨,最适合盐业生产。如果到五月底完不成全年生产任务,这一年的生产计划要想顺利完成,就很困难了。因为“秋晒”只有九、十两个月,温度原因,产量很低。因此,对于春天的生产旺季,场里高度重视,抓得很紧。层层召开动员大会,人人都要发言表态,一切行动听指挥,苦干巧干拼命干,不休假,不歇班,多为国家做贡献。全场上下,到处红旗招展,标语口号一片,广播喇叭反复播放厂长的动员讲话和职工代表的发言,一片大干快上的局面。场部还把走资派拉出来,与被管制的坏分子一起批斗一番,并用大卡车拉着到各队去轮番批判,名曰抓革命、促生产。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我感到漠然,一点儿也激动不起来。我不知道这政治挂帅管不管用,也不知道这阶级斗争是不是一抓就灵。相反,只觉得那些胸前挂着大牌子,被逼得低头弯腰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很可怜。
每天凌晨三到五点,是盐工最紧张最忙碌的时间。因为一天24小时,只有这个时段没有太阳,气温最低,卤水不蒸发,就选准这个时间收盐。第一道工序是“起盐”,就是用特制的大耙子,把水底的原盐搂起来。一耙子盐足足二三百斤重,双手紧紧抓住耙柄,用尽全力拽着耙子往后挪,把盐搂成一道道岭。我的力气不足,只靠两手拉不动,就在耙子上拴一条绳子,挂在肩上,用全身的力气拽。第二道工序是“推盐”,用木锨把盐装上盐场特有的独轮小推车,送到几百米远的滩头空地上。刚从水里捞出来装上车的盐,水还在哗哗得流,人在水中走,车在水中行。推车上池堰的时候,要弯下腰,用力推,否则上不去。过水沟的时候,车要通过不到一尺宽的“独板桥”,一不小心就会人仰车翻。第三道工序是“赶浑”,就是把起盐之后的池子里的浑水赶出去,把清水留下,这是盐工最拿手的绝活儿,我干得很漂亮。清理后池子里留下来的水叫老卤,再放上一部分新的卤水,五点多钟太阳出来,马上开始蒸发,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流程。这个安排的确很科学,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和空间。第四道工序是“打坨”,就是把收上来的盐堆成一个个圆圆的盐坨,每个坨子五六米高,大致有二三十吨。盐坨要用草苫子盖起来,避免淋雨化掉。几天后,县盐务局会来收购拉走。说实话,这盐工的活儿,既需要力气,也需要技术,一般人还真的干不来。
晒盐旺季最怕老天下雨,因为雨水落入盐池,卤水就会稀释,已经结晶的盐粒也会化掉,前面几十天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池堰和上下水沟渠被淡水浸泡也会坍塌。场部有人专门负责天气预报,一有情况,大喇叭立即广播。每到这时候,盐工们会毫不犹豫,一跃而起,冲进盐滩,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那叫“抢盐”。不难理解,辛辛苦苦大半年,不就是为了这点盐吗?在盐工眼里,盐场是他们的家,盐就是他们的命。
一连三四个月,盐工们每天都是这样干。没有人请假,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怨,大家都认为这样干是天经地义。没有加班费,没有奖金,没有补贴,没有会餐,那时候没有这种福利待遇。每到饭時,仍然是馒头、窝头、咸菜、稀饭,静静地吃完,倒头便睡。只有他们包括我自己,知道身上有多累。我不知道他们在拼命干活儿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不是有这样高尚的情怀。也不知道人们在吃到咸盐的时候,知不知道每一个盐粒都来之不易。我只知道,盐工,是天下最苦最累的工种。盐业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是世上最高尚的人。人这一生,只要做过盐工,就没有吃不了的苦,就没有受不了的累,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条公路穿过老八队,一头连着镇上,一头蜿蜒伸向远方,听说能到县城。我哪儿也没有去过,除了小时候生活过的农村,再熟悉的就是盐场,就是这老八队了。我经常向着公路眺望,经常看着偶尔驶过的汽车遐想,我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老八队呢?
14岁那年,我走出了老八队,到镇上读高中。父亲调到场部工作,周末也不用再替父亲干活。但是,就从这时起,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准盐工”。每到学校放假,我和同学们一天也不耽搁,立马儿到场里新建的工区“打零工”。住的是二十多人一间的大通铺,铺盖卷儿要自己背着去,吃的仍然是窝头和咸菜,干得活比“抢盐”还要重。在老盐工的带领下,我们每天早出晚归,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很苦,很累,但是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第一年的工资是每天一块四毛八,第二年长到一块七毛六,偶尔得到包工活,一天可以赚三四块钱。这样一年下来,靠假期打零工就可以赚到二三百元钱,我自己一年的吃穿基本就够用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对此坚信不疑。能够从十几岁开始就为父母、为家庭做点贡献,是我一生的自豪。
盐场的景色是美丽的。所有的盐场,总是与大海相伴。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边是湛蓝的大海,烟波浩渺,一望无际。一边是无边的盐田,波光粼粼,银光闪烁。海水、盐田、天空合为一体,分不清是水还是天。清晨,旭日从海面喷薄而出,将碧波荡漾的海水和盐田染得金碧辉煌,清爽的潮湿的带着淡淡腥味的风,吹拂着人的头发、面颊和身体的每一处,让人心旷神怡。傍晚,金色晚霞映照在大海和盐田上,让人立即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样精美的诗句。盐、盐田、盐场、盐工,拥有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生命,沟通了大海与人世,串联起古往与今来。面向大海和盐田,就象人的心灵面向着无限辽远。
后来,终于,我走出了盐场。沿着老八队门前的那条公路,我走进了县城,走进了省城,走到了很远。但是,我永远铭记寿光北部渤海湾畔那抚育我成长的盐场和盐工,不管多么繁忙,每年必须回去看看。斗转星移,盐场已经今非昔比,早已机械化电气化了,老八队的大屋早已不见,盐工们已经住上了楼房,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我爱大海,爱它那波涛汹涌的气势;我爱盐场,爱它那无边无际的胸怀;我爱盐工,爱他们永不停息的劳作。是那些淳朴的盐工,给了我第一份工作,教会了我怎样对待生命,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艰难和困苦。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干事,怎样为官。生命里有幸做几年盐工,是一生的幸运。
有付出就会得到拥有,有执着就会收获喜悦,有奉献就会拥有力量,有真情就会找到相濡以沫,有梦想就会有不倦的追求。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2019年3月1日于济南)